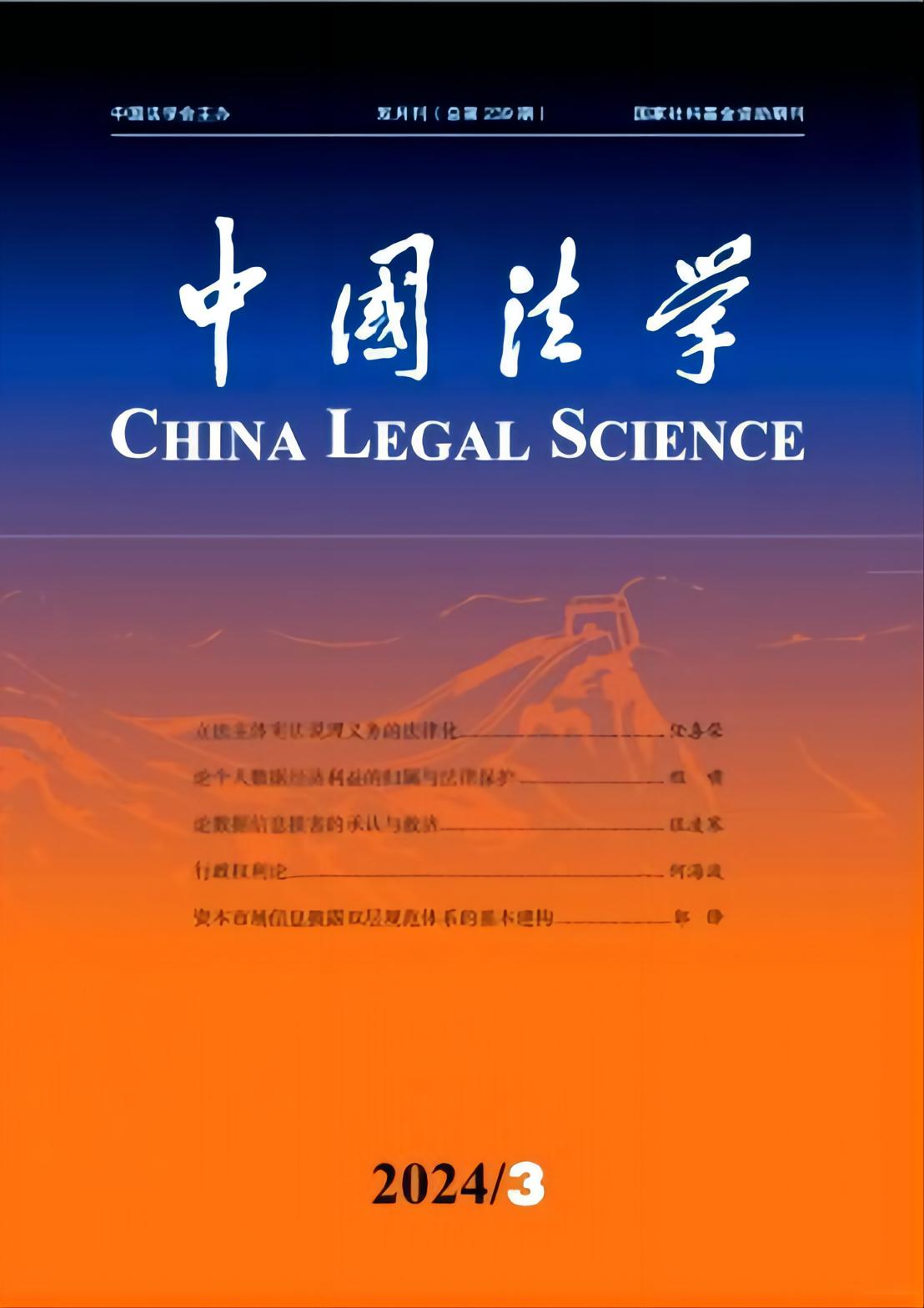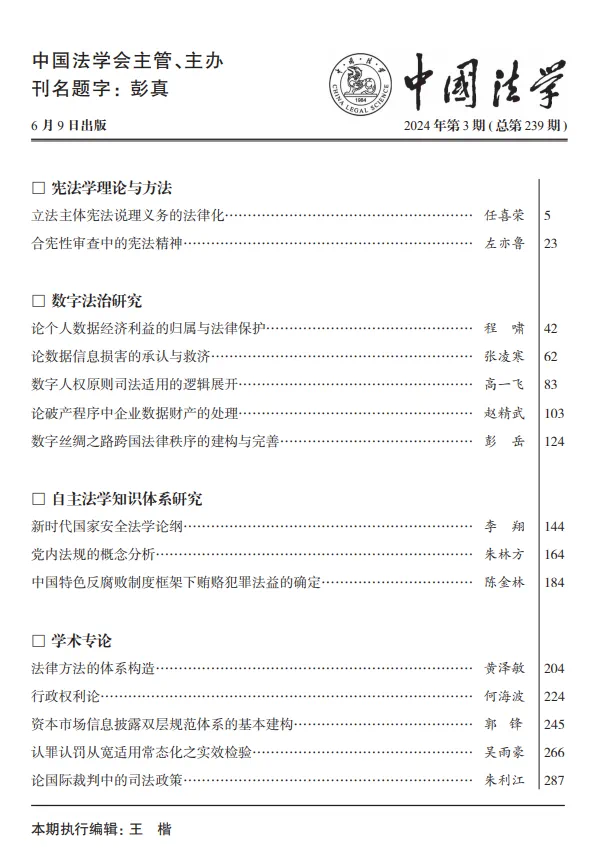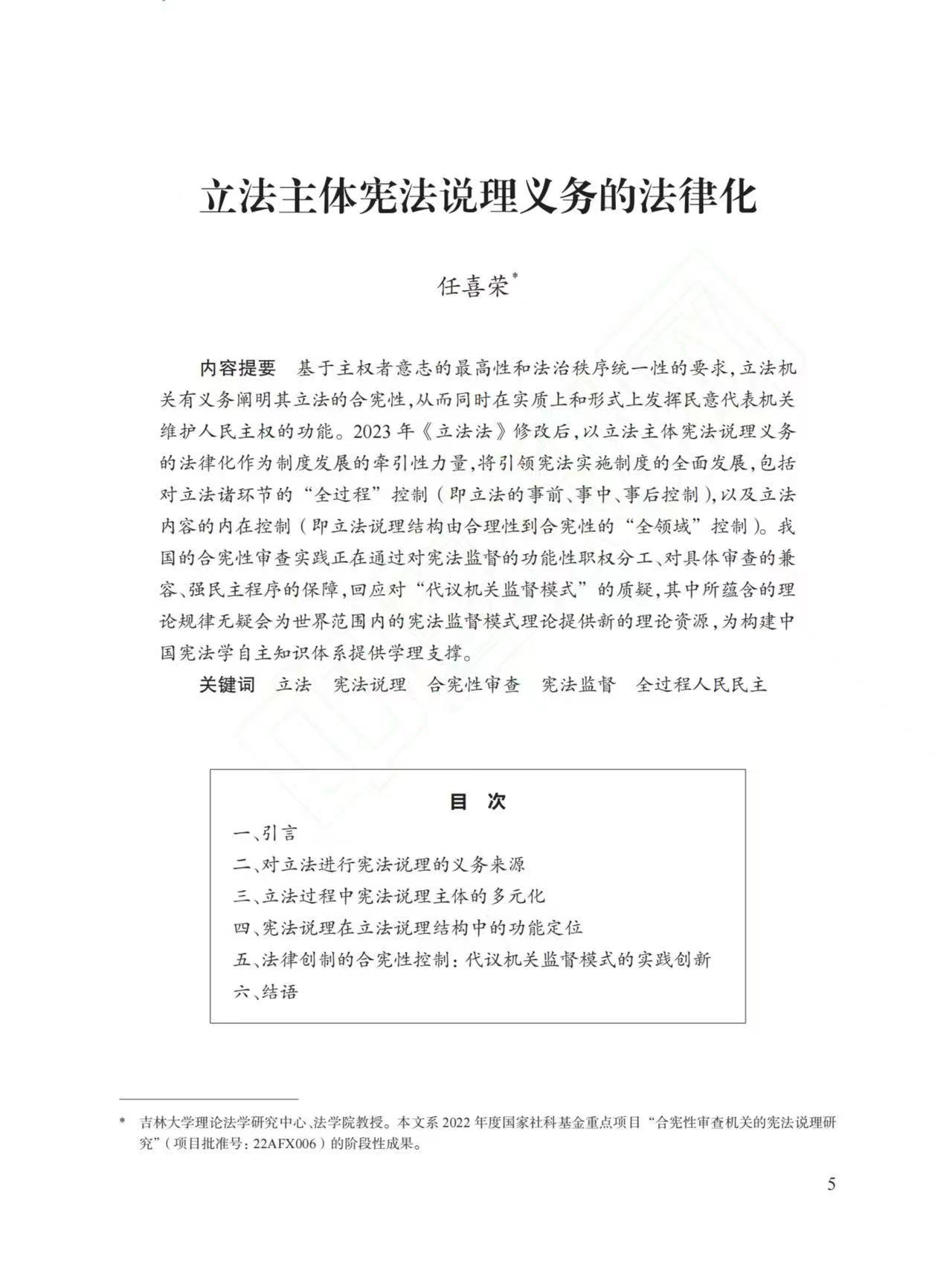近日,我校法学院任喜荣教授在《中国法学》2024年第3期发表题为《立法主体宪法说理义务的法律化》的文章。文章以202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为规范依据,以立法主体宪法说理的义务来源、主体多元、功能定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我国正在构建的立法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全过程”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实践创新。
2023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涉及合宪性问题的相关意见;对法律案中涉及的合宪性问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在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上述修改一方面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立法主体不仅要对法律草案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说理,还要对其合宪性进行说理;另一方面则将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以规范化的形式提前到了起草和审议阶段,与备案审查阶段的合宪性审查相结合,构建了我国立法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全过程”合宪性审查机制。
文章指出,基于主权者意志的最高性和法治秩序统一性的要求,立法机关有义务阐明其立法的合宪性,从而同时在实质和形式上发挥民意代表机关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以立法主体宪法说理义务的规范化作为制度发展的牵引性力量,将引领宪法实施制度的全面发展,包括对立法诸环节的“全过程”控制,即立法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以及立法内容的内在控制,即立法说理结构由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到合宪性的“全领域”控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正在通过对宪法监督的功能性职权分工、对具体审查的兼容、强民主程序的保障,回应对“代议机关监督模式”的质疑,其中所蕴含的理论规律无疑会为世界范围内的宪法监督模式理论提供新的理论资源,为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作者简介:任喜荣,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宪法学、立法学、法文化学。
文章概要
202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增加规定: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涉及合宪性问题的相关意见;对法律案中涉及的合宪性问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在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上述修改一方面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立法主体不仅要对法律草案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说理,还要对其合宪性进行说理;另一方面则将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以规范化的形式提前到了起草和审议阶段,与备案审查阶段的合宪性审查相结合,构建了我国立法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全过程”合宪性审查机制。
这种立法说理结构的变化,标志着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不再仅仅满足于立法主体以默示的方式形成合宪性判断从而实现立法质量的内在控制,而是对合宪性判断本身的说理过程提出了规范要求,从而可以使立法主体的宪法理性以形式性、程序性的方式展现出来。由于立法主体的宪法说理主要指向两个基本方向,即合宪性判断说理和宪法依据说理,其中前者在原则上遵循法律论证的逻辑结构,后者则在结构要素上包括政治正当性、宪法文本依据、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程序合宪等说理要素。这就使立法过程中的宪法说理可以发挥阐明宪法内涵、作出宪法判断的宪法解释和审查功能,成为维护宪法秩序一致性和融贯性的重要制度环节。以立法主体宪法说理义务的规范化作为制度发展的牵引性力量,反映出全国人大通过积极行使宪法解释权、在立法过程中开展合宪性审查、将民主程序与法治目标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宪法监督制度创新的努力。
对立法进行宪法说理的义务来源。“立法者有一种反映宪法的义务”,这是由现代国家宪法秩序的基本原则演绎出来的。关于我国立法主体的宪法说理义务,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可从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制度安排两个维度加以分析。基于主权者意志的最高性和法治秩序统一性的要求,立法机关有义务阐明其立法衡量的合宪性,从而同时在实质和形式上发挥民意代表机关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无法与其它权力割裂开来行使,从而在法理和实践上为在立法的全过程进行宪法说理提供了制度依据。
立法过程中宪法说理主体的多元化。立法说理的主体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论立场。如果依照宪法文本关于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主体的规定,则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作出具有宪法效力的宪法判断,并进行宪法说理;如果从宪法解释和监督职能履行的具体过程出发,则具体的职能部门和参与主体都可能依职责的配置而承担相应的宪法说理义务。前者更重视宪法文本中的权力配置及其效力,采取的是“规范—效力”的理论立场;后者更重视具体职能的实际分工及其履行,采取的是“职能—履行”的理论立场。从两种理论立场导致的结果看,前者往往坚持“单一”的宪法说理主体观,后者则必然采用“多元”的宪法说理主体观。2023年《立法法》的修改注意到了两种宪法说理主体观的互补性。其中,关于法律草案提出主体和审议主体对涉及合宪性问题进行说明的规定,是对“职能—履行”理论立场的部分采纳,使得中国宪法的职权型解释和监督在实践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
宪法说理在立法说理结构中的功能定位。立法说理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结构:即面向法的科学性的合理性说理、面向法的民主性的正当性说理、面向法秩序一致性的合法性说理、以及面向宪法全面实施的合宪性说理。一方面,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合宪性说理各有侧重、功能各异;另一方面,合宪性说理还发挥着将立法阶段的合宪性控制形式化、程序化的功能,从而使宪法全面实施的“全过程性”得以制度化。合宪性说理主要指向如下内容的说理:其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宪法依据说理;其二,法律草案提出主体就涉及的合宪性问题做出的与宪法相一致的“合宪”说理;其三,法律草案统一审议主体就涉及的合宪性问题做出的合宪性判断说理。
代议机关监督模式的实践创新。我国立法说理的立体结构展现出了立法主体对于法律创制过程,从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到合宪性的系统阐释的形成。通过加强立法阶段的合宪性审查,我国的宪法实施在整体上形成了包括在立法过程中进行宪法说理,通过民主赋权转化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解释,通过事先审查和咨询制度将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显性化,以及日益活跃的法律生效后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宪法说理义务的法律化作为制度发展的牵引性力量,将引领宪法实施制度的全面发展,包括对立法诸环节的“全过程”控制和对立法内容的“全领域”控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正在通过宪法监督的功能性职权分工、对具体审查的兼容、强民主程序的保障回应对“代议机关监督模式”的质疑。